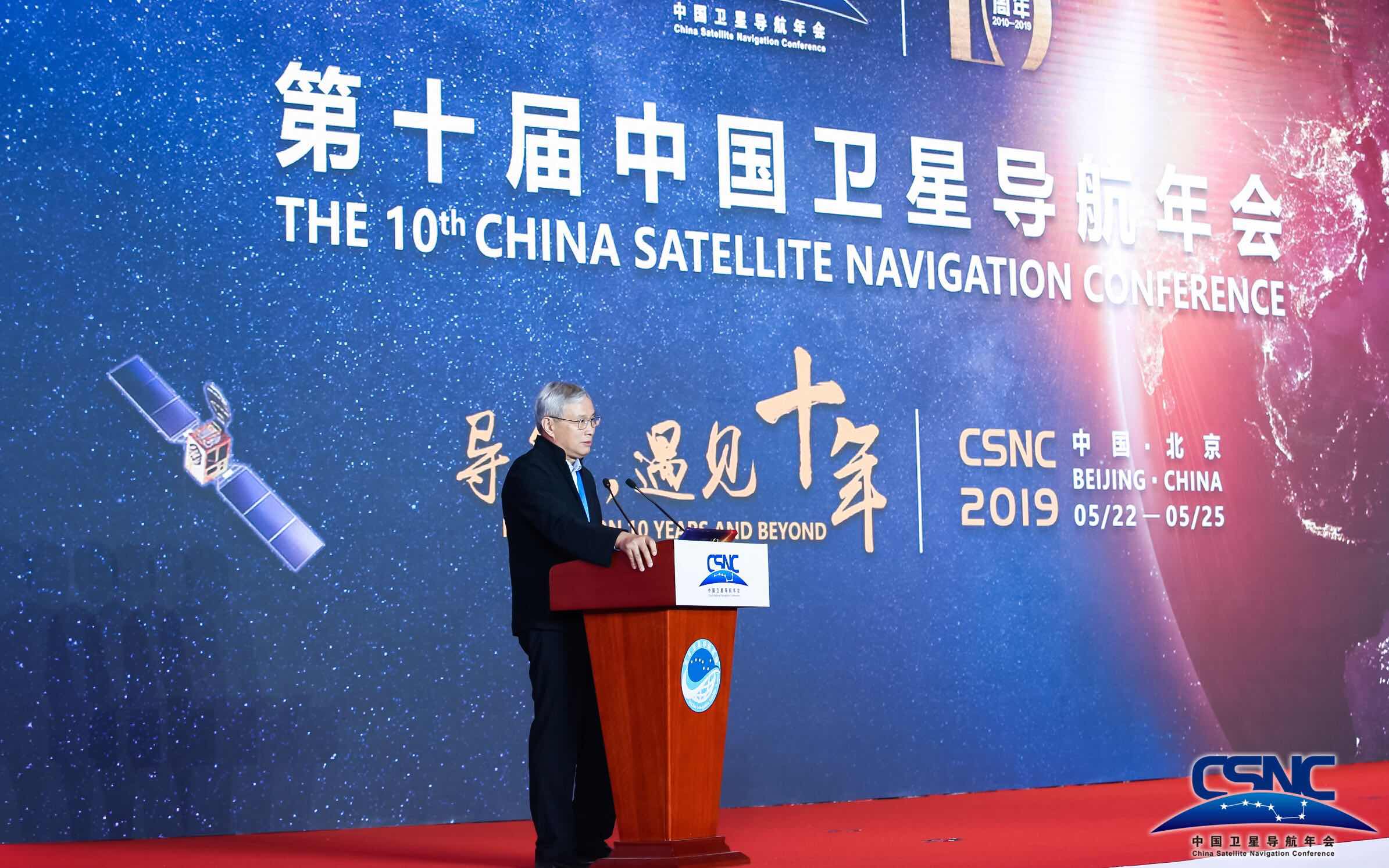
最近,我连续看了几家北斗应用产业有关的企业,有些感受,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些讨论,主要关心一个问题:后发经济。后发经济有很多麻烦,其中一个麻烦就是科技落后,国防落后,这就需要花很多钱。落后经济本来就是经济力量不够雄厚,不得不挤出力量来搞国防,搞军事;不搞国家没有尊严,搞呢这个钱要花出去,经济的其他方面的投资就要减少。所以这是一个后发的悖论。要发挥后发优势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北斗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例
那么看了这几家企业,结合北斗的实践,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例。
如今,卫星导航系统美国有,俄罗斯有,欧洲有,中国自己也要有。中国要有,就需要巨大的开支,那么这个开支后续到底有哪几种联结的方式?这个开支能不能带动更多的经济发展?多长时间,这个纯粹的国家安全开支会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机会,带动经济的增长?不仅提供就业、提供GDP,还可以提供税收,并提供进一步国防开支的基础。这就是要讨论的问题。
从一个相关的经验进行阐述,美国包括全人类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原子弹。原子弹原来是一个科学原理,涉及分子结构、原子结构及其能量的释放。原子弹一旦变成了一个技术,变成了一个可以应用的技术,它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就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原子弹的开发不便宜,当年罗斯福总统听了科学家的意见,担心法西斯德国先走一步,美国就用“曼哈顿计划”上了这个国家项目。据说原子弹研发消耗掉美国三分之一的电力:在当时情况下,美国的直接投资是20亿美元,动员了巨大的组织力量。 当然,最后这个效果是好的,先于法西斯成熟、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然后解决了二次大战的问题,提前结束了二次大战。
之后,倒过来,这就变成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当中一个巨大的决策的难题。美国有了原子弹,苏联也有了原子弹,美、苏后来又进入了冷战。那就要维持一个很大的军费开支来保持这种威慑。维护这么多的核武器、核弹头、核设施以及后续的研发,都是非常烧钱的。从这个经验看,有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维持巨大的军事开支的同时扩大民用,扩大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扩大向过去没有进去过的领域渗透,使之变成国民经济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另一倾向,就是维护很大的核武器开支,但是对它的国民经济应用重视不够,或者说重视以后进展不好,这就形成两个极端。
原子弹的弹头数量是苏联第一,美国第二;但是从综合的国力,包括原子武器这种巨大的投资引发的国民经济变化来看,美国做的比苏联要好。所以它是苏联后来一个很大的包袱。苏联军工很发达,但是国民经济、民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包括国家的财政力量,实际上在冷战当中耗到最后是失败的。我们要看看这个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其他方面国防开支、军事投资做出相应的政策,对这个题目作一些思考。
冷战和热战还不同,热战就是打,就是消耗,就是资源动员能力,比的是持久的消耗能力;可是冷战更麻烦,它不是马上打,但是你要保持威慑,对冷战时期的开支一点儿不比热战时候少,而且巨大的开支要年年维持着。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比如最近全球国防开支又升到了一个高度,这就对所有的后发经济,包括中国已经走到比较前列的发展中的经济,提出了很大的难题。
这里举一个核技术在国民经济应用的指标来看一看。日本、美国、欧洲,重视核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不仅是核动力、核电站,核动力的商用船、大型机械,关键还有核技术在其他国民经济很多领域的应用, 通常美国要占到GDP的45%。
我们知道中国的“两弹一星”是非常激励我们后人的故事。中国是1964年爆炸的原子弹,所以在核威慑面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站住了的,在核技术的广泛利用,比如核电站中国也走在了前面,但是在国民经济更广泛的、深度的利用方面,我们这个占GDP的比例还是蛮低的,0.2-0.3%的水平,跟美国大概还差一个数量级。
所以,我们在制定、落实国防开支方针政策方面,包括做相应的军民融合、产业化时,要引起很高的重视。这里要提炼出这样一个经济关系,即国防开支或军事开支,及其所带动的民用或GDP或财政力的关系。如果这两个力量有个良性循环,哪怕加以时日,那么这个国家,军事、国防是强大的,经济也是强大的,而且它可以变成一种源源不断的、可持续性的强大,可以形成军事和一般产业之间综合的国力。
从这个观点来看看我们北斗产业。在座的都是北斗的行家,北斗这个技术它也是大国争霸当中产生的。1957年苏联发射卫星,美国霍普金斯应用物理研究所的博士生,研究且接收到了这颗卫星的信号。该应用物理研究所与美国海军是一个长期研究合作关系,知道美国海军有一个需求:潜艇在运动中发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定位很重要,就问这两个年轻人:倒过来怎么样?既然地面接收系统可以定轨卫星,那么能不能通过卫星的信号确定观测点的位置?这是GPS诞生的缘由,它也是受大国争霸这种实际问题的驱动。
如果说GPS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巨大的耗费,几十颗星打上去以后很快启动民用。我刚才看了北斗应用产业的展览,北斗一开始就定下既是国防需要也是国民经济的需要,从技术设计和产业设置上就已经做了这个安排,这是非常正确的。然后你看美国的GPS,一方面给军用,一方面给民用,而且在政治上、道义上它都是得分的。因为1983年大韩民航的飞机误入苏联领空被击落,美国总统就借这个机会宣布GPS对民用部分开放,然后就是无偿开放,全球开放。
今天,我们从这个经验来看,我们是后发,GPS先行。对于后发,我们要看到目前形成的产业规模,就是GPS在全球到底有多大的经济规模?有不同的估计:总体是4500亿欧元,也有直接与间接的算法,准确的比较保守的估计是1000亿美元,是千亿美元级的产业应用。我们国家呢,应该是千亿人民币的产业应用,大概是这么一个量级关系。这就带出一个问题:下一步从国民经济角度来看北斗产业化,它是非常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一方面这本身就是一系列国家在高科技研发的一个基础,同时它要持续追加投资,所以它的产业化做得好不好,是全球舞台上在这个方向的竞争,一个持久力的问题,一个可持续的问题。
北斗的双重后发与两种不确定
我最近看了这5家北斗应用产业的企业,很受教育,基本看到了两个东西。第一,双重后发。不光是这个技术、这个起步于军用的技术,我们是后发;这种军用技术怎么民用、怎么产业化,我们也是后发。同时,面对两种不确定。第一个不确定,因为这种核心技术不会慷慨地完全给我们,它要封锁,它有壁垒。我们在技术上能不能在高精尖度达到可以跟美国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可以领跑的水平,这个问题不确定。第二个不确定更麻烦,就是产业化应用,因为GPS的民用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理论上1983年就开放了,实际的开放过程和各国的发展到广泛使用还更晚一些,但是已经搞了很多年了,已经成了很多老百姓、普通机构、普通设施一个应用的习惯了。它又是免费的,已有的装备、已有的终端已经投资了,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有一个北斗系统的产业应用,到底多大程度上可以渗透进入这个市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加快这种渗透应用,这个不确定。
当然目前的形势客观上对这件事情有推动,特朗普只要“断供”,那就可以大大推动北斗的应用。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要想到,他要是不“断供”呢,不把他那个胡闹的“断供”模式沿用到卫星导航这个领域里来,那我们就面临后发,这个后发不仅有后发的优势,也还有后发的麻烦:GPS先行,它已经布局了,它已经渗透了。所以我们这些企业从各个方向来探索,我看到两个东西是非常好的。
第一,就是中国的这批公司,在机制上很新。虽然北斗是一个国家级的项目,就像当年我们两弹一星是国家级项目一样,但是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改革开放,你看我们原子弹的民间应用,那还是单一的国有制在推动,无论是原子能电站还是原子能的其他应用,真正在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的推进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所以后发的更晚。但是北斗今天有条件,我看过的5家公司,4家是民营的,一家是央企但是已经运用了民营的机制,包括允许管理团队参股,持有一定的股份,让这个公司的长远发展与管理、技术开发人员有更加紧密的直接的挂钩,决策有更大的自主性,这个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面对的是一个极不确定的市场。虽然这个技术现在的普及程度比20年前、30年前大不一样,但是它能不能在中国、在一带一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能够得到普及,得到比GPS更好的行业应用和大众日常应用,这个事情不确定,而这个不确定是需要充分利用民营企业的体制优势,决策快、利益直接、容易重组。利用这个机制,而且筛选非常无情,打的上去就上去了;市场如果不认账,那就得下来。这一点我认为是北斗产业发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
第二个支持点,我在这几家企业跟企业家去谈,我觉得中国的企业真是积累了这么一股劲,你看像这个四维图新,开始做地图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法律框架都不清楚,地图是保密的,地图就不准民营机构随便去碰。在这种情况下有市场需要,有国际参照,就开始做地图,这种测绘的商业应用过程,用于测绘的车辆都被扣过,都被受到过审查,都得到过怀疑,当然我们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一路过来,很容易理解,但是这很不容易啊!你像北斗星通公司当年开始搞卫星导航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个事情能变成产业,没有人相信可以用股东的钱往这个方向做芯片的开发,能不能见到收益更是非常渺茫的。但是也几年、十几年这么往里砸。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今天,往更好的产业化来支撑我们国家的国防开支、安全开支,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微观经济基础。
北斗可以向传统产业学习
在这几家公司座谈交流当中,我们还提出一个看法可供在座的各位参考,就是要向其他传统产业学习。我们是一个高科技,其实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这一路走来,开始不会的所有的产品都是高科技的。那怎么能够从后发逐步走到前头去,这里头有一个从已有的中国经验吸取力量的课题。
第一个问题,争取后发优势有没有意义,人家已经有了,从人类范围看不就是重复建设吗?这个重复建设到底有没有意义要回答,中国的经验证明有意义。我是1988年第一次去日本,回到北京机场,那个行李传送带上一个接着一个是日本的家用电器,当时中国就没有。那你说日本它有产能,咱们中国人用它的产能不就行了吗?事实证明不行。出国团组人员是因为有一些外汇、有一些额度,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买不起的。如果没有中国在上一批企业家上中国的家电,投资-改进-便宜,应用面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宽,而没有这么宽的应用面,即便人家不卡脖子,不提高技术壁垒,我们能享受这种现代科技的人口规模都是很有限的,要提高这个规模,速度也是很慢的。同时从里面再开发出新的技术,那更要节节往后推啊!
所以从全球范围看,不要认为只有从0到1很伟大,从1到N也很伟大,因为它可以让人类的很大的一个后发人群,享受当代科技的成果,加快进入现代化,同时在享受现代科技成果的同时,积累研发力量,也对人类的科技研发、积累作出贡献。
仔细来看,我们这张后发路线大概是一张什么图呢?大的范畴就叫看了才会做、才会造。人类的制造就是两个途径,一个是想到了造,一个是看到了造。后发就是看到了造,但是看到了造也分很多步,第一步是看到了也不会造;第二步是会造但造不好;第三步造得好但价格不一定便宜,但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穷的优势、成本低的优势,提高在全球市场上杀价议价的能力;第四步是价格低但质量够不好,然后就提升品质,不仅提高制造的品质,同时也提高服务的品质;第五步就是从1到N登堂入室,倒过来参加到全球从0到1的研发当中去。大家看看中国的洗衣机、冰箱、彩电、手机、通信基站、汽车、无人机,等等等等,走的都是这么一条路线图!当然, 如果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的话,是可以把某些台阶走得更快、把某些后来的台阶提得更早。
这个值得北斗的产业化加以参考。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在价格、品质、批量上要实现的一个优化组合。早年中国造的东西,价格便宜,东西就不够好。其中最大的一个变量就是批量不够大,只要批量大,不但可以薄利多销,而且可以从批量当中积累、提升品质的经济能力。所以现在看来,这个三元组合:价、质、量看来是对的,在北斗产业化当中要特别需要加以考虑的一个组合。
这就是我发现的成果,就是科技,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化当中要注意的那个广化,注意那个广化的程度。什么叫广化、广度呢?就是多少人可以享受你这个技术,在多快的时间内让多少人可以去享受这个技术。这件事情不但有技术意义、经济意义,还有社会道义的意义。大家想想看,为什么美国的国力后来有后发优势,很快超过工业化英国,超过欧洲国家?美国产业里面有一个历史上应该值得记忆下来的贡献,就是通过福特流水线的发明,把一个产品批量可以做到成本最低,可以让它的蓝领工人买得起在欧洲只有贵族、上流人物、有钱人才能够享受得起的物质,这是美国国力后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IBM也好,微软也好,戴尔也好,包括后期的中国联想也好,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就是让全球数亿人可以用上电脑,如果按照发达国家先行的品质、价格走,这数亿人就会长久挡在PC这个门外。中国的海尔、格力、美的、科龙在历史上写下的一笔,就是不但会造,而且造的品质也可以,同时使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买得起、配置得起。你看看中国所有家电的普及,它是非常重要的当代的一个产业的一曲高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华为、小米、OPPO 、VIVO,智能手机包括原来的传统手机,从0到1都不是中国公司的贡献,但是中国公司在整个手机武装全人类上,武装亚洲,包括印度、越南,武装非洲,在这个进程中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而且由于这个贡献有这个量,尤其是电子产品用户的体验和用户的反馈,变成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路径。所以只要有量,它的品质改善提升是非常快速的,同时积累的经济实力,就允许像今天华为的P30,已经在性能上、品质上都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智能手机媲美,可以在某种程度领跑。再看看我们的支付宝、微信支付,是服务领域当中从后发走到前头去,你可以说互联网、商用互联网也不是中国公司的从0到1,但是由于我们人口规模巨大,应用广,渗透快,普及程度高,这些特征就使得这些产业都成为全球范围内响当当有竞争力的产业。
那第二个问题呢,这里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要强调华为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以客户为中心。高科技很了不起,但是高科技的产业和企业容易染上一个缺点,就是显示我的技术水平,而不是从用户角度看怎么帮人家解决问题。但是全球范围看,所有伟大的全球公司,最厉害的不仅仅是技术,而是善于把这些最先进的技术用来解决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问题,日常生产的问题,解决普通人的痛点。
我最喜欢的一个高科技英雄叫张小龙,是微信团队研发的领头人,因为我很早访问过他,他的设计理念,他的技术开发理念,我认为是值得我们所有搞高科技的企业家和工程师加以参考。张小龙当年开发微信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他跟他的团队反复强调,说这个产品出去,不要让用户觉得我们了不起,要让用户觉得他们自己了不起。这是他的开发思想,不是要把一个科技炫而又炫的东西作为一个拿下市场的杀手锏,而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用这个技术帮你解决,而你的感受是你自己解决了,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技术的产业应用的准则,而它就出在中国公司当中,也难怪微信差不多拥有十亿的用户,这都是高科技产业化当中了不起的贡献。
我也访问过滴滴,滴滴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是移动互联对于匹配出行当中的供求。你要车,车找你,互相找不着,移动技术包括我们的定位技术帮了忙。但是滴滴最了不起的是它怎么把这个技术能够说服传统的汽车司机能用上,那么最早是磕了一百几十家出租汽车公司的门,一个一个被拒绝,最后才发现出租汽车公司老板同意也没有用,司机不接受。当时的司机很多是40、50后的年龄,对新技术不敏感,手里也没有智能手机,怎么让他们装上这个滴滴打车的软件,还要怎么让他们去习惯使用?滴滴真正厉害的故事,是他们最早创新开发的员工,包括老总在内,都是跑到北京西客站在出租汽车等候的那条通道里头,一个车窗、一个车窗敲下来做工作,找到最快的办法说服出租车司机会用。说服完了,还是没有人打车怎么办?他们就掉过头来,自己拨号打车,就是这么去启动一个市场!所以高科技能不能落地,不在于这个技术多高,是在于这个技术跟市场、跟用户、跟普通人,跟数量极其广大的老百姓的那个用户的结合,这是真正伟大的高科技公司能够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
北斗产业到底怎么定义?
所以,最后我就有一个问题,提供给北斗这个产业化的进程,大家一起来思考,到底怎么定义我们北斗这个产业?到底是GPS有,我们也要有,万一它“断供”,我们也要不让中国人的定位、导航受到丝毫的影响,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这是不是我们应该给自己定义的一个“下线”,我们是不是应该根据这几十年中国产业、科技的发展,以及新的进程,还可以定义一个“上线”,就是既使美国不对我们在GPS这个领域“断供”,既使它继续向全球提供免费的、优良的民用服务,北斗也要在全球范围内可以提供更高水平、应用面更广、宽度更大的产业应用,真正为人类享受现代导航定位这个技术,为这个伟大的目标做出中国人的贡献。

Comments are closed.